中间声音|亚洲小型艺术出版实践的一些趋势

中间声音
编者按:北京abC书展正在这个周末如火如荼地进行,abC书展是国内最早起步的书展组织者之一。受疫情后“摆摊热潮”的影响,国内艺术书展蔚然成风,如此多的独立出版人、独立书店、艺术家、艺术机构等参与到这场夏日联动。这种文化为什么会突然如此生机勃勃?我们可以如何讨论地方性出版文化?如何讨论小型出版实践的内在价值?小型出版实践会对出版业带来什么改变?韩国The Book Society/mediabus出版人林庆勇(Kyung-yong Lim)从中间美术馆于2017年制作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何为亚洲性?》一书中获得启发,来重新想象亚洲的小型出版实践。本文为展览“出版作为方法”(2020.10.30-12.20)的同名书籍前言,由我们与AP Project联合翻译。
亚洲小型艺术出版实践的一些趋势
林庆勇
“有一种新的潮流是:‘如果你在国内找不到可以交谈的朋友,那就到别的地方去找。’”[1]
找一个既不会引发争议也不会引起其他问题的点子并在此基础上做项目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们今天要说的项目的两个关键构成概念恰恰就由争议和问题组成。当谈到图书或出版时,我们往往认为自己很了解它们。然而,如果给它们加上形容词“小型的”或 “独立的”,它们就会立刻变成争论的对象。人们很容易问:它们与已有的各类图书有什么不同,或者这类工作的价值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应该根据提出问题的语境来解释。很多时候提出的问题是好的,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毫无帮助和空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提问。即使已经有了既定答案,我们也可以在想象小型出版的过程中找到许多种定义和用途。
“亚洲”的概念也是如此。亚洲很大,定义也很模糊,但我们经常使用“亚洲”这个词和这个概念。如果有人认真地询问亚洲是什么,它所传达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没有人能轻易地回答出来。亚洲的地理分界和文化上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共同体来认识和理解。无论是地理上的实体,还是想象中的共同体,亚洲都是一个需要不同学科一起协商讨论的复杂概念。
自2008年我在首尔开始艺术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以来,亚洲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小规模的艺术出版文化,蔚然成风。我们很难了解其他国家的城市发生这类活动和实践的背景,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以举办艺术书展的大城市为中心,书展大大促进了图书的流通。在全球化时期,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交流是很正常的,但这种小型出版活动的活跃还是一种相对新的趋势。
为什么这种文化会突然变得如此生机勃勃?廉价航空或线上社交软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过去无法想象的一种对周边国家的意识,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变得能够想象“亚洲”这一概念。随着围绕双年展的国际交流计划和项目的增多,相邻地区之间形成共同议题的局面或许也有助于亚洲概念的普及。毫无疑问,这些临时性活动所建立起的网络是活跃的,但很难预估它会如何持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类交流通常是偶然的,很少会延续成一种稳定的交流。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这类出版活动进行个案研究,特别是那些把出书作为自己实践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最终目的、或把出书作为相互交流的媒介的这类出版活动。书籍可以成为交流思想和建立共同议题的重要媒介。这些人是怀着怎样的想法和目的来做书、开展书籍的交流?
要讨论地方性的出版文化,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出版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这一历史背景[2]。关于参与图书制作的各方,我们可以大体描摹出一个出版行业的流程,如印刷厂、发行公司、书店等,这个流程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参与书籍内容生产的人也是如此,如作者、编辑、设计师、制作人等。从20世纪初胶印机发明和出版业刚被建立时,这个流程就开始全面运作。小成本生产上万本书成为可能,所谓的知识产业诞生了。从18世纪开始稳步建立的西方大学,为这个行业提供了稳定的资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商人们在全世界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在后续几十年里被我们称为出版发行的这些密集编织在一起的网络,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
日本思想家酒井直树不同意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关于亚洲哲学的论断,特别是关于中国和印度哲学的论断,胡塞尔认为:“印度或者中国的哲学很难被归为正宗的‘哲学’,因为印度和中国哲学家对生活的态度不是真正‘理论化’的。”[3]考虑到胡塞尔是一位抵制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具有批判性精神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知识分子或西方的文化圈中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根深蒂固。中国思想家孙歌强调“亚洲”作为概念存在的必要性,但她同意酒井直树的观点,认为需要消除在过去几百年间长期支配着亚洲的欧亚地理分界线,以颠覆统治了亚洲过去几百年的欧洲中心主义[4]。孙歌认为,我们需要的亚洲并不是像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里的人民那种感觉上的共同体,而是把亚洲扩大为“亚洲式”(something Asian),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思考。

《普遍性与特殊性:何为亚洲性》

Archive Books出版的英文版封面
无论如何,很难将小型出版实践置于亚洲的普遍概念之中。我们可以猜想,这样的出版实践很难依据地区或主题归类,即使有可能,其差异性或独特性也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消失。针对这个问题,孙歌在她的讲座《创造新的普遍性》(2018)中提到的由美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定义的“相似性”概念,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线索。孙歌将相似性理解为不同于相同性或同质性的概念,认为相似性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可以对应起来的相似元素,而是去掉了彼此相似的部分后还仍然存在的核心差异。此外,她还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特殊性中内在的固有差异来获取另一种普遍性[5]。
基于这样的讨论,我想从普世(universality)价值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亚洲”各地区中各种可以被称为“小型出版”的实践。从我开始研究亚洲地区的小型出版以来,我时不时就能找到个体实践的案例,但很少发现把小型出版作为一种话语结果来讨论的研究。普遍性(universality)并不是我们常想的那种抽象的价值,而应该是孙歌所提出的“另外一种普遍性”。在这样的对于普遍性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产生“亚洲小型出版”的话语,并进行进一步研究。
本书目录中收录的大约五十个的亚洲小型出版的条目,都是我们在首尔和亚洲几个城市的活动中建立过联系的人。与其说这些人是传统出版领域的专家或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不如说他们是基于新的地域意义或技术来开辟新空间的人更为准确。比如亚洲,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对纸媒的玩法就像玩Ins、脸书或抖音等社交媒体一样,基于这样的态度,他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出版物。然而,大多数人觉得类似的例子只是个别案例,或者将其视作被称为“亚洲性”东西的一个结果。它们的独特性得到了承认,然而基于差异的“相似性”却没有被讨论。
提出“亚洲性”和“小型出版”的议题,是为我们介入我们自身的状况提供方法,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利用这些状况。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建立孙歌提出的新的相似性的其中一个角度来讨论。这种做法原可以视作对西方现代化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的抵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亚洲”和“小型出版”的概念,并以合适的方法来研究与定位个体实践。
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本土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强调了出版物在塑造共同体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解释了“情感共同体”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中,“情感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想象和感受” [6]。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阿帕杜莱认为始于现代化初期的印刷文化促进了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形成,它促使了印刷资本主义的建立[7]。那小型出版又会塑造怎样的情感共同体呢?
自从19世纪亚洲地区开始现代化,领导印刷资本主义的就是各个地方的精英,尤其是那些曾在殖民主义国家留学的人,他们为塑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而挣扎。我们可以设想,相比之下,现在领导小型出版的个体所塑造的情感共同体是更加碎片化和边缘化的,远非立足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共同体。
这本书也收录了展销场(Display Distribute)的何颖雅(Elaine W. Ho)谈到的K-pop粉丝影响特朗普竞选连任事件的文字[8]。为什么那些消费与政治无关的文化产品的人——比如消费韩国流行音乐文化(K-pop)的人——会做出反对特朗普的政治判断?在许多个原因中,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是如何表现出与基于民族、国籍、国家或语言等传统身份形成的团结感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团结感。换句话说,韩国流行音乐粉丝们的政治团结表明了一种在“身份政治”失败后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种团结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另一种方式形成的、不以印刷品为媒介的情感和政治的共同体。
曼谷的出版团体ซอย | soi解释说,他们的实践更接近于“参与”或“重新想象”,而不是“干预”。这样的实践强调不依赖已有的分类和地图,而是想象地区的地理状态及其所属的环境。尤其是当下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地缘意义摇摇欲坠,这样的状况更促进了这种需求。我们一直将亚洲想象成一个有着几十年相互交流的邻里,但我们现在明白,这种交流不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交流是否永久消失了呢?让我们提一个问题:在疫情中真正受到威胁的是什么?相比亚洲意识或者思考共同体的可能,难道不更应该是运载上百万人和数十亿货物的资本主义的物流吗?印尼出版团体“进一步阅读”(Further Reading)将亚洲理解为“可能成为的东西”(could be)。要将亚洲视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区域,我们需要从重新考虑曾经赋予我们熟悉感的全球化意识开始。穿着优衣库或Zara的衣服、用着苹果手机,并不能给我们一种同质感。相反,记住亚洲国家之间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记忆显得更为迫切。
非常规节奏避难所(IRA)的成田圭介说,在通过小型出版而与几个亚洲国家保持联系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一个地域可能有着令人不适的现实,比如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记忆和历史。同时,大多数这样的交流项目都是由公共资金控制的,这是很有问题的,这使他们必须考虑投资方的政治立场。然而,这种情况也可以成为重新认识亚洲的机会。比如活跃在亚洲乐坛的直升机唱片公司(Helicopter Records)的朴大贤,因为受到日本DJ组合Soi48的启发,找到了自己对亚洲音乐的兴趣。Soi48搜寻并收集古老的泰国音乐,在俱乐部里奏放。对朴大贤来说,这就是一个亚洲人想象其他亚洲人的过程。在这里,相比找到亚洲人之间的共同情感,排在更前面的动机是亚洲人通过互相观察意识到彼此的差异。韩国的朴大贤、日本的Soi48和泰国的老音乐之间形成的关系,可以说是“亚洲式”的东西。
解放发行
在亚洲进行小型出版发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已经完善建立起服务于小型出版的书店和发行体系的欧美不同,亚洲还未建立专门发行此类书的机构。在首尔,小型书店或美术馆书店正在逐渐增加,但是它们的规模还不足以应付各种小型出版。小型出版也很难使用预先存在的发行网络,因为它有发行系统上的要求,比如要有ISBN书号。因此,在许多亚洲城市都设有临时的艺术市场,例如艺术书展,许多书籍通过该渠道得以发布。但是,小型出版的发布不仅仅涉及书籍的销售,它也涉及到特定语境下出版社的实践应该被如何介绍和发散出去,这与书本身的特点是直接相关的。
2020年的疫情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图书发行步骤。它使依靠面对面进行的发行方式遭遇了危机:书籍发行网络不仅可以将书籍分发开来,也会导致病毒的传播。台北傻瓜书日(Fotobook DUMMIES Day)的林君烨预计,新冠肺炎的蔓延趋势可能会影响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方式,并反而可能会增加人们想要面对面买书的欲望。这是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得越久,面对面交换书本的愿望可能就更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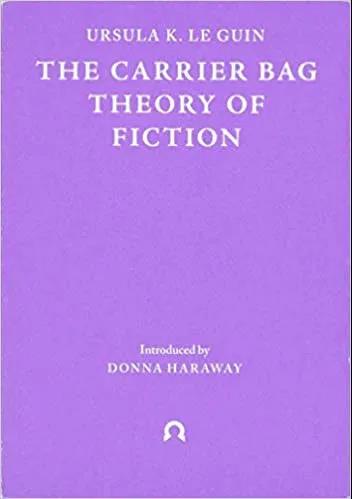
Ursula K. Le Guin: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
香港的出版团体“展销场”在亚洲做小型出版发行,尤其通过“后勤慢递”(Light Logistics)——一个由单人寄送书籍的独特发行系统,他们称之为“人对人发行网络” [9]。何颖雅仔细记录了运输程序并在网站上做了发布。她将这种过程比作“一种奇怪的现实主义,包括将事物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的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 [10],这是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她的《小说的背袋理论》[11]中做的解释。勒古恩讨论的现实是与科幻小说有关的,但正如她暗示的那样,如果这里有一种现实是我们通过发行小型出版而建立的,这会不会与她说的现实有某种相似性?勒古恩因对它描述如下: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实主义,但现实本就是奇怪的。
像所有严肃小说一样,经过适当构思的科幻小说,无论其多么有趣,其实都是试图描述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真实的行为与感受,人在这个巨大的口袋里、在宇宙的腹部、在孕育未来事物的子宫和埋葬曾经事物的坟墓中,如何与其他一切相关联——它讲述着这个无尽的故事。在其中,也如在所有小说中,有着足够的空间容纳人类于他的所属,于人所处的事物发展的位置中;也有足够的时间,来收集许多的野燕麦并播种它们,为乌姆唱歌,听乌尔的笑话,观察蝾螈,而故事还没有结束。仍然有种子要收集,有着装有星辰的包里的无尽空间。[12]
声明立场的出版
正如俄语词Samizdat(意为“个人出版”) [13]所显示的那样,小型自出版通常被用作表达个人在其所属社会中政治姿态的媒介。对于Samizdat,俄罗斯激进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科夫斯基(Vladimir Konstantinovich Bukovsky)写了一句很巧妙的话:“我自己写作,自己编辑,自己审查,自己发表,自己分发,自己在监狱里度过。”[14]
尽管布科夫斯基的话被认为是夸大其词,但一些亚洲国家仍然会限制出版自由并且实行审查制度。这是因为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活动,在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中起过一定作用。这些出版物大多数是以我们称之为“杂志(zines)”的传单形式的小型出版。同时,这种媒介还可以用作个人或小团体展示自己的兴趣和与他人交流的一种手段。东京的自出书人聚会(Tokyo Zinester Gathering)、不规律节奏避难所(IRA)和福岛出版团体野蛮人书籍研究所(Institute of Barbarian Books),他们使用那些传达自己政治信息的杂志,但主要还是用这些小型媒介来表达自己。
ZINE COOP的成员彭倩帼(Beatrix Pang)解释说,由于杂志是由个人或一个团体制作的,因此这些人应该全面了解杂志的制作过程,确定什么是可能放进去的或什么是不可能放进去的,什么资料是可以使用的而什么是不能使用的,以及如何安排这一切工作和发行事项。在这种背景下,小型出版的发行便使我们想到一些特定的场所。比如遍布在亚洲各地的“信息商店”(infoshop)就具有一种价值,使不同城市通过杂志形成一种松散的团结。信息商店,例如东京的IRA,香港的ZINE COOP,首尔的Café Byulggol以及新加坡的Wares,都通过类似但各有特色的方式来制作和发行杂志或小型出版。正如“信息商店”的名称所展现的那样,无形的信息和网络本身与实体书一样重要。

日本非常规节奏避难所,图片来自timeout.com
ZINE COOP的项目“自由之书Burning Ixxues”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约20个国家的自出版团体(zinester)寄来的约100种杂志[15]。参加这些活动的自出版团体以寄杂志的方式支持该倡议,经ZINE COOP收集后于2020年在首尔等地举行了展览。这证明,小型出版也可以创造政治上的团结,那些出于不同目的被创作出来的“个人”杂志也可以被自发地放置在这个语境之中。
类似于用小型出版宣传政治态度的做法,也有人用小型出版来宣传多样性文化或非传统观念。新加坡设计工作室及出版社“临时出版社”(Temporary Press)的邝文达(Gideon Kong)和杨伟羚(Jamie Yeo)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涉及到与艺术和设计有关的非传统观念时,小型出版所带有的隐秘的政治参与可能比显而易见的政治冲突更为有效。这个观点使我们想起了有关创作形式和内容的长期辩论。在新加坡的政治背景下,小型出版可以被看成一种更隐蔽表达自己的方法。这让我们想起了塞思·普莱斯(Seth Price)关于前卫艺术的讨论。
当然,经典的前卫艺术之所以有趣、激进,是因为它倾向于避开一般的社会交流,通过别人难以理解的内容自我放逐,但如果它的目的是利用大众传播流通,它就会立即变得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前卫艺术不仅要有流行文化的传播机制,还必须有流行文化的一般形式。当罗德尼·格雷厄姆(Rodney Graham)发行流行歌曲CD或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出杂志时,艺术界人士必须得承认,这些东西有着与消费市场上其他产品一样的艺术姿态。但是差异性也存在于这些产品内部!这些产品蕴藏着文化产业的密码,而它们包含的某个乌托邦时刻正指向着未来的转型。[16]
尽管小型出版不能成为如流行歌曲或卡特兰杂志之类的公众传媒,但它可以借用流行文化的形式将真实嵌入其中。正如邝文达和杨伟羚所说,也如在开罗和安曼开展出版实践的“怎么样”(Kayfa ta)以“怎么做指南”为形式表达出的批判立场,小型出版的政治潜力将通过各种转变得以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小型出版的政治态度和审美取向也会通过与其自身状况相结合而产生。同样,这样形成的迂回路径也可以被其他使用者改变。
纸张作为技术
小型出版的代表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小型出版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停地使用各种技术。但是,就像使用Xerox印刷机和骑马钉装订的杂志被认为是小型出版的代表形式一样,对于首次尝试生产这种出版物的人来说,印刷技术的选择很重要。尽管印刷方法通常由预算决定,但是在发行领域中,有些印刷技术的确是受到偏爱的。
来自“临时出版社”的邝文达和杨伟羚选择了孔板印刷(risograph)作为他们可使用的印刷方式。印尼的“进一步阅读”使用孔板印刷来印刷文本为主的内容,这是因为它在印尼的价格较低,而且在国际上流通时,孔板印刷获得的独特品质也能得到认可。位于首尔的酒吧和出版机构Seendosi使用孔板印刷来制作艺术家画册。这种工艺在过去主要被用来制作教堂周日礼拜的公告或学校的考试手册。就像转色印刷这种老工艺成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重要媒介一样,探索新的印刷媒介并探索其潜力在小型出版非常重要。
由台北傻瓜书日编辑出版的《观看之道:通过写真集和自出版来阅读东南亚》(A Way of Seeing: Reading Southeast Asia Through Photobook and Self-publishing)一书中也记录了这些情况。他们研究了出版的基础条件还不完善的东南亚地区的自出版。这些地区的自出版人使用了易于使用且价格低廉的技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上演了许多有趣的实验。
再者,小型出版文化的意义之一是它加强了社交网络。例如,我们制作杂志是为了传播特定的内容,但也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杂志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一种被我们称为“后数字化”状态的动向形成了。意大利媒体研究学者亚历山德罗·卢多维科(Alessandro Ludovico)以金·卡斯科内(Kim Cascone)提出的“后数字化”概念来解读当前的印刷文化,并提出了各种可以将互联网特点运用到纸质书中的策略。当然,这与是看纸质书还是电子书无关。互联网建立的连接使我们不可能回到数字时代之前。人们不可以想象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互联网使超越国界,语言和时间的网络成为可能。
那么,小型出版是否可以作为方法之一来成为重新设定科技与人类之间关系?尹元华(Yun Won-hwa)将加速主义哲学家对技术的立场解释为“形成另类视角的小说,形成盗版书指南,形成非传统的平台,形成未来的情景,同时妄用和滥用现有技术并重新定义其功能,并最终对整个世界进行重新设定。”[17]尽管这是关于加速主义哲学家的讨论,但考虑到小型出版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小型出版中找到这样的看法并非没有根据。
实际上,公众对小型出版的理解是复杂的。有的认为小型出版指形式独特、价格昂贵的书;另一种看法是形式更灵活、不需要纸张的线上网络素材。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被理解为在当前条件下为促进流通采取的策略。Adocs在线发布小型出版的PDF格式出版物,其中许多出版物都是已停产或仅在线发行的书籍。Min Guhong Manufacturing的Min Guhong为书籍进行策划和编辑,他的工作是“寄生”于图形设计工作室“工作室出版社”(Workroom Press)旗下的。我们通常将纸和网络理解成不同的东西,但他认为应该用“新规则”来将纸本和网络放在一起理解。
尾声
项目名称“出版作为方法”借用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竹内好在1961年以“作为方法的亚洲”为题的演讲[18]。他将亚洲作为方法“为了更大范围实现西欧的优秀文化价值” [19]。他认为,东方可以通过“一种文化或者价值的反击” [20]重新包围西方,从而改变西方本身。我们2000年初开始策划和发行书籍时,参考了许多在荷兰和德国的活动个案。许多出版社仍在策划和制作优秀的书籍。我们为将这种文化介绍给首尔和亚洲其他地区而努力。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发现了在亚洲不同地区以各种方式进行实践的出版人,我们留意他们的实践和他们制作书籍本身的故事。我认为我们在介绍韩国以外的出版书籍和出版文化时,对本土文化或其含义的考虑不够充分。如果在香港出的一本书品质很好而且我们想进一步介绍它,那我们只需把它带到韩国就可以;但是,这种方式更接近于“移植”而不是“交流”。甚至直到几年前,我们都不愿承认全球化时代的亚洲本身。
2019年,在新加坡、香港、沙迦、台北、上海、北京、广州参与艺术书展和与朋友见面的经历使我们了解到,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人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出版实践。我们并不是声称亚洲的小型出版将会更普遍,或它将以欧洲的小型出版那种程度流通。如果竹内好先生还在世,他可能会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发掘的领域具有唤醒小型出版内在最好的价值的能力。我希望这个项目是一个起点。
参考文献
[1] 摘录自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第五章“亚洲作为方法——超克「脱亚入美」的知识状况”(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54.(译注:中文版由行人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2] 相关讨论内容可参见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3] 酒井直树(Naoki Sasaki),《什么是亚洲?——有关人类学差异》,《普遍性与特殊性:何为亚洲性?》 (Berlin:Archive Books,2019),8. (译注:中文版由北京中间美术馆于2018年翻译编辑)
[4] 孙歌,《创造新的普遍性》(2019),《创造新的普遍性》,Han Yun-a译(Seoul:mediabus,2021),5–6.
[5] 孙歌,《创建新的普遍性》,12.
[6]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中的“此时此地”(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6)(译注:中文版由三辉图书/上海三联书店于2012年出版)
[7] 阿帕杜莱,“此时此地”,8.
[8] 何颖雅(Elaine W. Ho),Getting a Move On: A Logistics of Thought toward Print and Publics (继续前行:从物流视角思考印刷与出版), Publishing As Method. (Seoul: Mediabus, 2021).
[9] 后勤慢递(Light Logistics), https://displaydistribute.com/haukun
[10] 何颖雅(Elaine W. Ho),Getting a Move On.(继续前行)
[11] 乌尔苏拉·K·勒·金因(Ursula K. Le Guin), 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 (虚构的背袋理论,1986). 前言 Donna Haraway, 插图 Lee Bul (UK: Terra Ignota, 2020).
[12] 乌尔苏拉·K·勒·金因, 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虚构的背袋理论) 译者注:原文中引用小说内容由Nomadia韩文翻译,引用自https://nomadiaphilonote.tistory.com/2.
[13] Samizdat是冷战时期活跃于东欧将出版作为政治活动的激进实践。相关资料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mizdat
[14]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 To Build a Castle: My Life as a Dissenter (垒墙筑堡:异见生涯回忆录)(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9).
[15] zinester一词指制作杂志的人.
[16] 塞思·普莱斯(Seth Price), Dispersion (分散)(2002). http://sethpricestudio.com/writingarchive/DIspersion.pdf
[17] Yun Won-hwa, Gumeongeurobuteoui soyongdori (漩涡),或参见 雷札·內加勒斯坦尼(Reza Negarestani)著作 Cyclonopedia, K-OS (Seoul: Mediabus, 2020), 144.
[18] 译者注:原文作者参考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韩文版,翻译Seo Kwang-deok,Paik Ji-woon, (Seoul: Somyong Publishing, 2004);中译版可参见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熊文莉译,高士明、贺照田编:《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
[19] 英译见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什么是现代性?竹内好的思考》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书中“作为方法的亚洲”章节, 165.
[20] 竹内好(Takeuchi), “作为方法的亚洲”,165.
作者介绍
林庆勇,独立出版“书社”(The Book Society)的主理人、出版人、译者、策展人。现居韩国首尔。在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和韩国电影艺术学院主修电影研究和电影制作。他在2007年创办了一家名为mediabus的小型出版公司。2010年,他联合成立“书社”,这是一家书店和项目空间,推广艺术书和各种主题的独立出版物。
韩文/英文 翻译:Vicki Sung-yeon Kwon
英文/中文 翻译:孙杲睿、倪嘉
中文编校:孙杲睿、印帅、黄文珑、张逸杰
微信排版:闵锐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