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回忆和躲藏——以录像为媒介细读“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展
“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2021.4.22-5.21)是中间美术馆以2021年画廊周北京为契机,正在798艺术区D10临时空间举办的展览。该展览由来自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美国、德国、瑞士、波兰、荷兰、乌克兰、俄罗斯、捷克、克罗地亚、智利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在1980年代的实验性创作构成,作品形式包括录像、文献记录片、摄影作品及雕塑。展览将于今日闭展。 在本文中,我们以录像为切入点,细读展览中的几个作品,希望可为已经到场或不能到场的观众提供以文字深化体验的可能。
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主要娱乐形式由静态的书籍、杂志、期刊转向运动的画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电力的普及,电影和电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开。1960年代,索尼推出了第一台面向个人而非公司的经济型录像设备,为大众进行个人纪录提供了可能。自北美起,越来越多的实验电影创作者和观念艺术家开始运用这个媒介进行创作,探索录像的内容、物理实质、边界及时间这一维度,介入观众对运动画面的消费并改变观看体验。进入1970年代,行为艺术家们也开始尝试用录像带记录自己的行为作品以将其传播覆盖更多的观众。他们也直接用录像机代替观众,面对镜头完成表演。1980年后,随着剪辑技术的进步、心理学中“意识”概念的复兴和音乐电视频道的创立,录像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吸引了更多的创作者。
在798画廊周展出的“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的展览里,录像作为此次展览的主体,既作为行为表演的纪录,也作为文献档案和一种艺术形式,它扮演着丰富的角色。本篇文章将选取展览中的几个作品进行细读,讨论艺术家们如何将录像的特性进行挖掘运用以契合他们的艺术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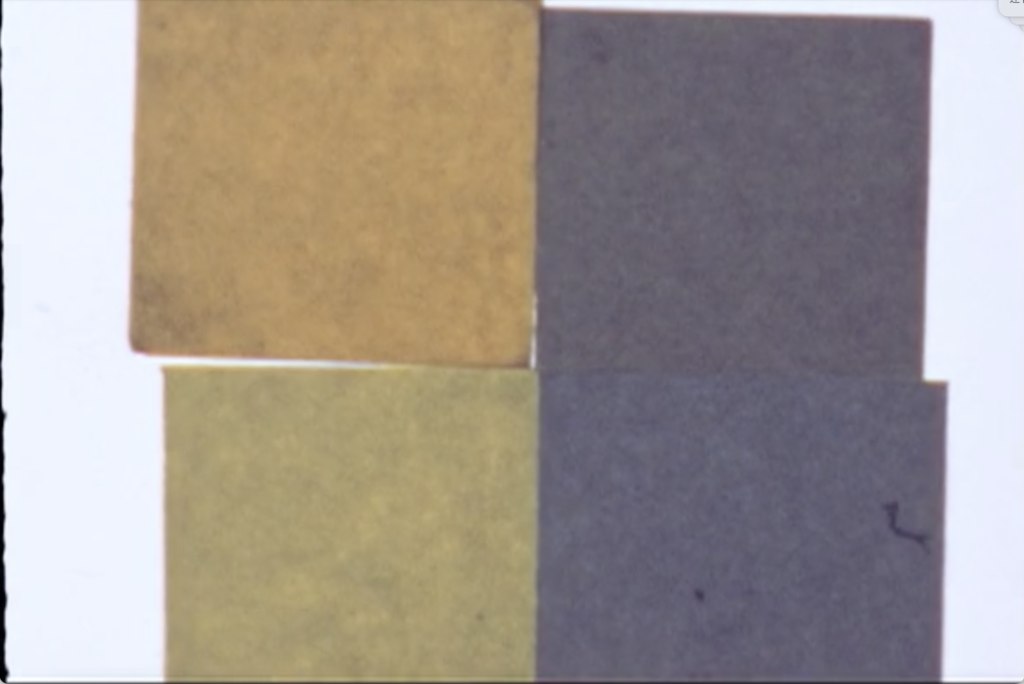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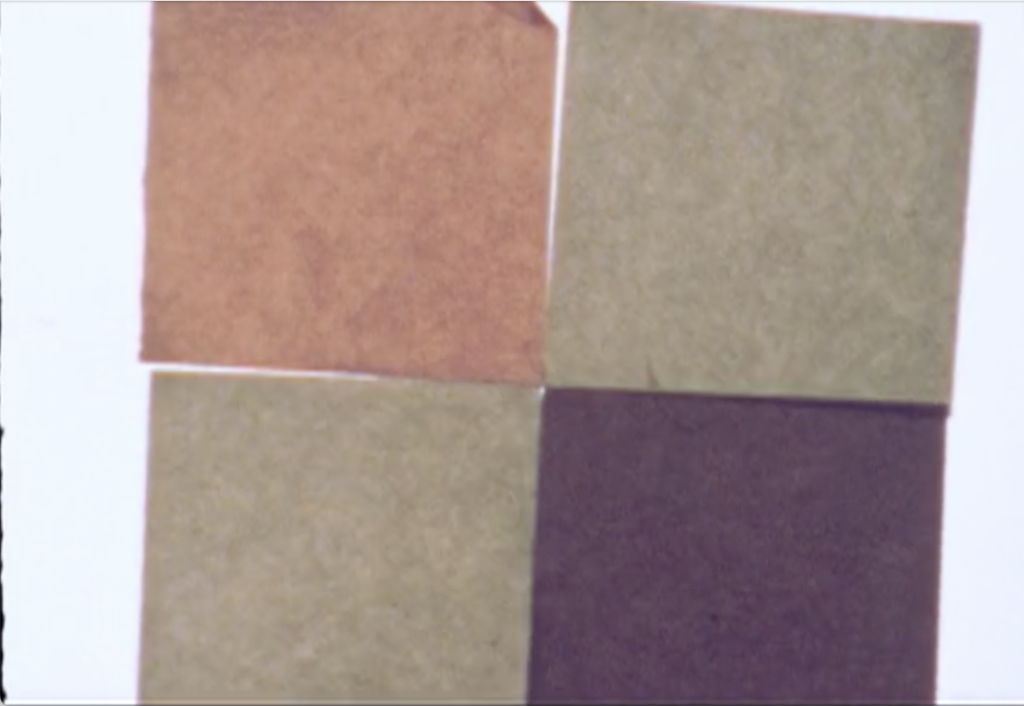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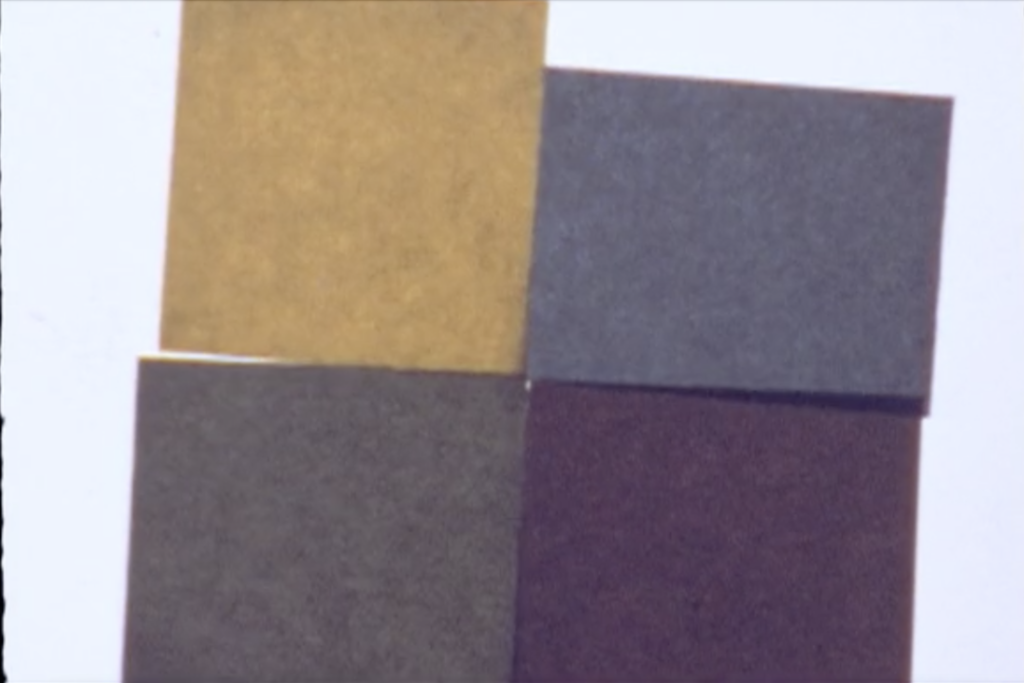
冈崎乾二郎,追忆维特根斯坦,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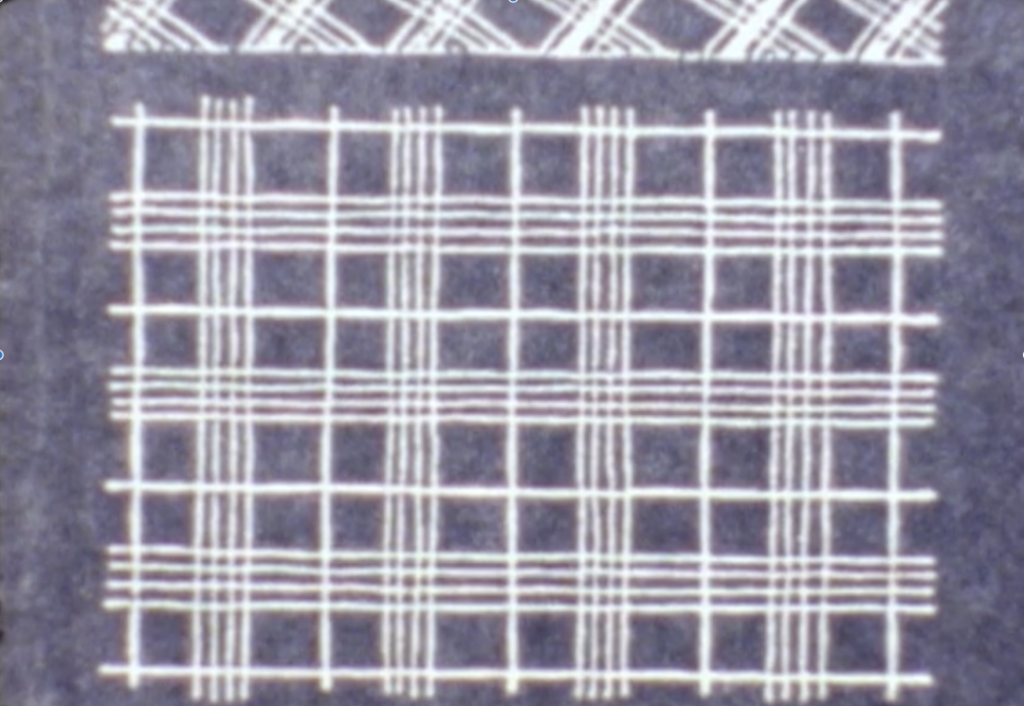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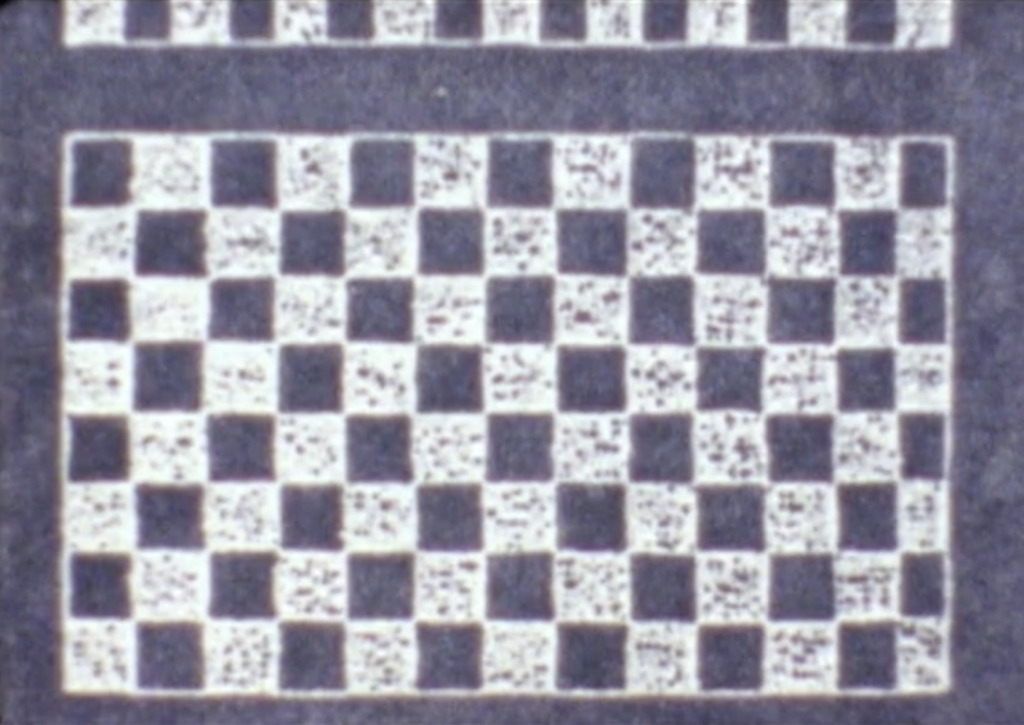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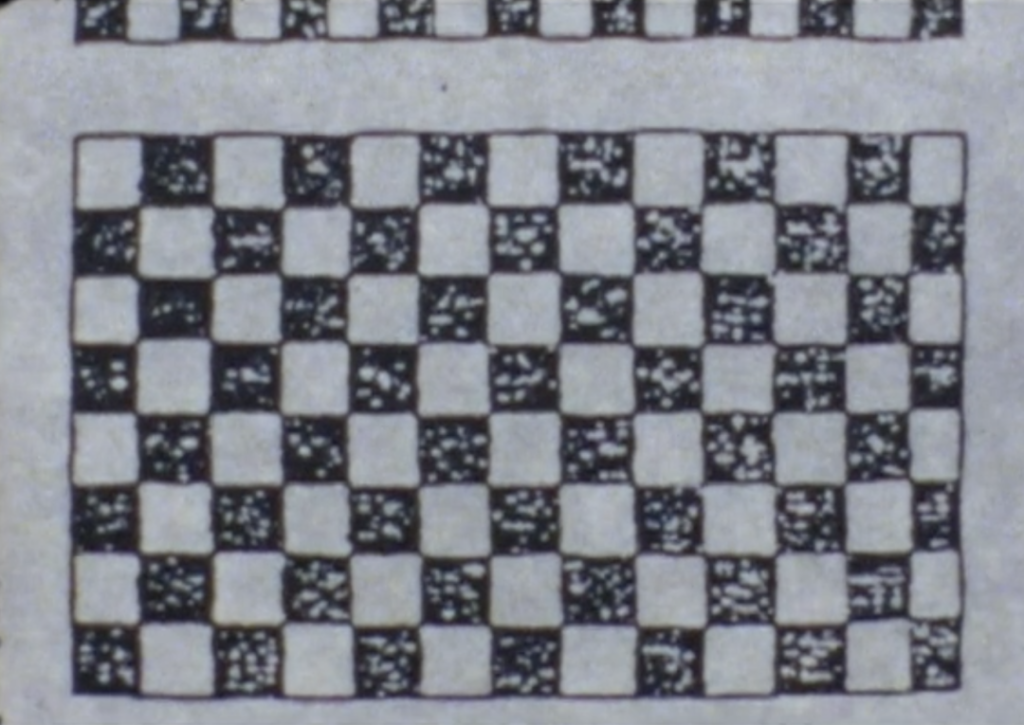

冈崎乾二郎,追忆维特根斯坦,1988
在展厅一众用视觉意象完成意识或潜意识叙事的录像作品当中,艺术家冈崎乾二郎的作品《追忆维特根斯坦》这个对录像本身进行形式探索的作品显得格外突出。他尝试质疑视觉信息中被不假思索接受的语言性。艺术家通过剪接8mm胶片来探索图像和文字的关系,用图像间的拆解重组、文字和图像间的对照、重复和基于相似的差异性指向语言和图像更细微的具体使用和录像这一媒介本身的可能性。作品同时探索时间维度上图像的“动态性“,打破录像里常规的时间流速,运用剪接的手法对内嵌在录像本身中的图像、时长、格式等要素作出提示。影片的内容、速度、文字、颜色和图像间的承接,都是艺术家进行拼合探索的语言信息;而艺术家选择用轻松惬意的日常图景和漫画风格完成作品的主要主体表示 “正与语言陷入激烈的交战”、“用如此粗糙的语言无法阐释精密的问题”的焦灼。正如艺术家运用自比的维特根斯坦之口所宣称的那样“如果存在一个能把所有事物记录下来的录像世界,那没有被记录的只有录像本身了”,冈崎乾二郎尝试记录“录像本身”。事物和“事物的录像”、本体和表意之间的距离,被 “录像”这一“表意”本身拆解和在不同语境下重构的过程中,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使用”被打破和重新塑写出来。
永子与高丽,裂变,1980
除了录像视频创作和对录像形式的探索,展览中也有不少行为纪录。在永子与高丽的《裂变》中,录像机以现场观众的角度忠实地纪录了他们的完整行为表演。在这种具有剧场性质的视角里,世贸中心、哈德逊河堤、垃圾填埋场等公共场地占据画面中心作为舞台,艺术家们以这些地点的历史意义、城市职能为行为表演提供牢靠的注释。白旗、冲锋,他们的表演充满着战争的隐喻,横亘画面的哈德逊河堤是冲锋的前线也是休憩的战壕。白旗既是冲锋的旗帜又是包裹身体的柔软抚慰,同时常常引出两个舞者之间承担牵绊拉扯的张力。他们将标志物做个人化解读,又将个人投身于社会使命。而异化的躯体和支离脆弱的动作也让整个表演充满个人色彩,两个舞者之间感情的流动覆写了宏大的背景。他们向纽约世贸中心发起冲锋,狼狈得依偎、治愈、眺望、受伤、直到两个躯体滑落垃圾填埋场的坑洞里。永子和高丽的作品充满着对战争和暴力的反思以及个人情绪上的愧悔和自伤,投降性和无力感埋藏在貌似可怖的表象之下。如果说暴力是不假思索打破界限的力量,那永子和高丽暴力的可能未曾发出便被自行收回,更让他们异化的躯体显得更加沉重、不合时宜和孤离。这是一次背负着历史的艺术家个体在公共场域内进行的个人化情感表达,这种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强烈共存感在这段表演中处处可见,也因此显得格外动人。
除此之外,通过录像这一传播媒介,观众难以体会现场观看永子与高丽作品的临场感;而在《鸟》这一作品中,“临场性丧失(non-presence)”这一影像的特性,恰恰成了作品完成的关键。
沃齐米日·博罗夫斯基,安杰伊·米坦,切扎里·斯坦尼谢夫斯基,托马什·威尔曼斯基,鸟,1985
在《鸟》中,四位波兰艺术家们将七个鸟笼带进展览空间挂在墙上,然后将鸟笼打开驱赶出在里面本不愿意离开的45只活鸟。在鸟全部离开鸟笼之后,一位艺术家在空间里进行了一段激烈的声音表演,最后以另一位艺术家在入口处钉上一块木板结束。而在第二天的展览里,艺术家选择展现行为的“影像”,而非“展现行为本身”来完成这个作品。艺术家在展览入口处播放前一天录制的录像,而观众进入展览场馆后,只有木桩上坐着的鸟迎接他们,而不见艺术家和笼子。录像机录制的是“曾经存在过”的事物。在《鸟》的作品中,录像的这种自身属性被艺术家运用的淋漓尽致。录像中激烈声音的 “曾经存在”,述说着声音、艺术家和鸟笼此时的“不存在”,二者相互印证。而展览现场的“安静”,也是在突显声音的“已逝”。当第二天入场的观众们只与无辜的鸟群面面相觑,不能不觉察到艺术作品中微妙的讽刺意味。
而艺术家设计让观众与录像和鸟群先后相遇,这种空间上的位移伴随的强烈时间感受,由观众自发的“回忆”进一步加深。面对鸟群时,艺术家的撤出给了观众作为主体行动的机会。“回忆”作为人们对已逝事件的追思,重现了录像画面 “曾经存在”的意味。而回忆里板子封门的结尾也由空间封锁延伸到时间和记忆的不可封锁。当观众面对鸟群想起曾见过的录像,回忆带来的主观时间与此身所在的客观时间相互叠加。联想到当时紧张的政治,让人恍惚何时是此处,此处是何时?这种用录像和现场塑造的时间叙事,仿佛是对历史的总结,对现实的慨叹,也仿佛是对未来的预言。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体验不可能在另一个场域里再次重现。即使如此策展人依然选择展现艺术家当年抗争的声音,虽然单纯个体声音的展示并不能给予观众自发互动的空间,但从导览册对这个完整作品的描述中,还是可以窥得一二。
“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与其他参与者相比有着特殊的自治性质。类似艺术家在《鸟》当中的自我设计;同样“利用”了艺术家身份完成表演的,还有集体行动小组这一艺术群体。
集体行动小组,在远处散步的人是行动的附加要素,1989
在《在远处散步的人是行动的附加要素》这一作品中,集体行动小组通过群体行为对“组织者”与“群体”的关系作出隐喻,而非纯粹的自我表演。行动的组织者邀请12位参与者到郊区的浅坑旁,坑里放着12只装着闹铃的信封,分别标有参与者的姓名;铃声在参与者到达时开启,等到电池自然耗尽结束,组织者将参与者引到浅坑旁开启闹铃后离开,在参与者“目之所及”的远处散步,而参与者在浅坑旁等到自己的闹铃停止后才可离开。整个视频模拟参与者的视角进行拍摄:他们(我们)看向浅坑里不知何时停止的闹钟和浅坑旁同样不明所以的同行者,一边互相交谈,不时看向远处的组织者,一边等待自己的闹钟停止。观众和所有的参加者一样,迷惑而无目的,直到影片最后粗略地介绍了这项活动,才让整个事件清晰。组织者“不加解释”的背影让参与者的迷茫无处安置;而在这种随机武断的框架下,时间除了被人“渡过”,没有任何额外的意义;一切追问都在行为设计下显得如同不合时宜的自问。这种闲散日常、看似漫无目的的举动下是艺术家对社会和生命现状本身的反思。
有趣的是,参与者的迷茫既是这个作品内涵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巧妙地(讽刺地)成为了集体行动小组持续艺术实践的最好保护;看似无意义的随机举动帮助小组逃过克格勃的严厉审查。从这个维度来说,跳出这个作品本身,集体行动小组对“迷茫”这一状态现实又机敏的运用恰合他们公民身份和艺术家身份的双重叠加,这使得集体行动小组作为一个艺术实践在更长的时间和历史概念上另有其意义。由此,录像的延时性既是完成并揭示这个作品意义的重要部分,也是集体行动小组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的12位参与者完成了这个作品,但由于无法窥知作品的全貌而不能成为作品的观众;这使得这个行为只能通过录像的形式传递到它真正的观众那里。
除此以外,策展人有意让每个场域内的作品彼此稍有关联,但作品之间些微的相关之处又使得差异感尤为明显,从而避免了一种过度“沉浸”的体验,借以提醒观众自身所在之处。而《巴黎公社小组生活档案》、《海迪·布赫尔在废弃精神病院的影像资料》等传统意义上作品文献的展出,也是策展人一直以来意在模糊行动实践和创作作品的理念践行。

展览现场
撰文 朱思宇
校对 张理耕
编辑排版 祝天怡














发表回复